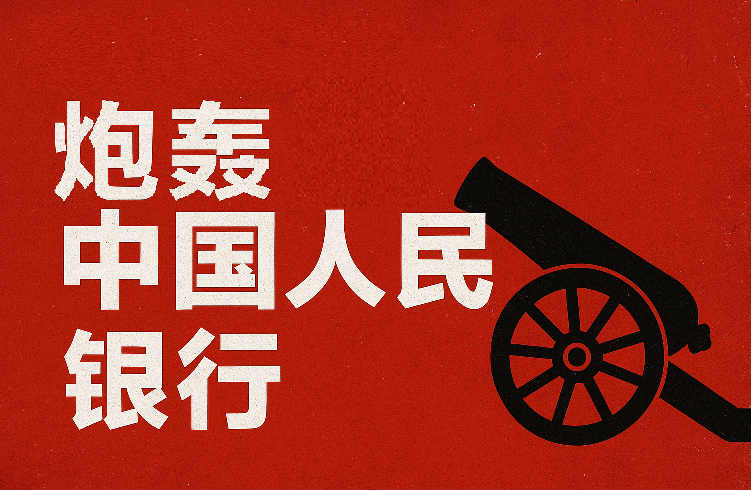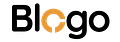导语:9月以来,官方与央行层面高频宣示“全球治理倡议”与“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”的政治意图与战略自信。文章立意宏大、措辞壮阔:要为全球治理贡献“中国方案”,要以更公平的国际金融秩序取代“现存不公”。但话语与现实之间,往往横亘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本文点评这些宣示的逻辑与事实基础,指出其中的夸大、混淆与潜在风险,并给出更接地气的判断。相关官方文本与国际文件可参照:央行与官媒发布、在“上合+”会议讲话以及IMF/IMFC会议材料等。
一、宣示 ≠ 公共产品:话语的权威不等于制度的合法性
潘功胜行长的文章与国家领导层的倡议,都把“全球治理倡议”定位为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”的高地。这一话术有其政治效果,但“公共产品”的要件不仅在于倡议,还在于透明规则、第三方监督、长期可预期的制度安排与广泛国际共识。单方宣示可以塑造话语场,但无法自动创造他国的信任与制度承诺。国际货币治理的历史告诉我们:谁来提供规则、谁来承担责任、谁来接受监督——这些都需要漫长的制度化过程,而不是一次宣言就能解决。
二、国际货币体系变革:人民币“上位论”与SDR化身主导货币的两大误判
(一)人民币“稳居前三/第三大支付货币”的说法并非等同于“可替代美元”
官方与部分论述强调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提升,甚至将此视为挑战美元体系的证据。确有进步:人民币跨境使用、双边本币互换、CIPS 等基础设施扩展都在发生;一些国际大行(如汇丰)也加入了CIPS 等网络,推动人民币结算便利化。可这些是局部与增量进展,并非等同于全球储备货币与主导结算货币的替代。SWIFT 最新统计显示: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仍在低个位数(2025年7月约2.9%),远低于美元与欧元。官方与学界应避免把“局部增长”夸大为“体系替代”。
要点:货币国际化依赖的是市场深度、可兑换性、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法治信任——这些不是单靠清算通道与试点就能立刻建立的。短期内,人民币在区域链条与双边贸易中角色上升是可见的,但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仍有重大缺口:官方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仍小、以人民币计价的可交易资产不够深、私营部门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与信任不足。
(二)把SDR当“超主权货币”寄予厚望,是理论善意与现实约束的错配
理论上SDR可以弥补单一主权货币的缺陷;但SDR并非货币,而是一种储备资产与记账单位,其能否承担日常贸易计价与私营部门结算,受限于流动性、市场工具与结算机制的缺失。IMF近年来确有推动SDR在官方层面更广泛运用(例如用于MDB资本补强等创新用途),但把这些步骤等同为“马上替代美元”的路径,是政治性乐观。要实现SDR广泛化,需要解决常态化发行、私营市场参与、以SDR计价的深度金融市场与结算网络等一系列技术与政治难题。
结论:人民币国际化与SDR扩展是两条不同路径,现实推进都需要时间、市场与国际共识。把“货币体系变革”简化为“技术+政策宣示”是不够的。
三、贸易结算与跨境支付:结算货币多样化 ≠ 去政治化
原文把“跨境支付多元化”“数字技术提升效率”与“脱离政治工具化”联系起来,但技术不是魔法棒。
- 技术提升只解决效率问题:CBDC、区块链、智能合约、二维码互联等,确能提高结算速度与降低成本,但它们无法自动消除制裁风险或司法管辖权问题。支付的控制权、合规(AML/KYC)与司法可及性,才是能否被“武器化”的根本因素。俄罗斯被大规模制裁后出现的案例表明:当关键金融节点(如大型 correspondent banks、美元/欧元清算渠道、SWIFT 等)被限制时,即便存在替代技术,贸易与金融活动仍会遭遇严重阻碍。最近的现实样本显示:为规避制裁的关系链往往转向“易物、走私、现金与影子通道”,这些并非“正常化的技术替代”。
- 新支付网络的规模与互操作性仍然不足:中国的CIPS、QR互联试点、部分CBDC跨境实验都在做,但与全球主流结算体系(日均量级、参与行覆盖、深度流动性市场)仍有差距;并且CIPS大量依赖国际通讯与资产清算生态(例如仍借助SWIFT 报文等),说明所谓“脱钩型”替代并非完整孤立可行。
要点:跨境支付的“多元化”有利于分散风险,但并不自动等于“去政治化”。在地缘政治冲突下,真正发生的是支付模式与交易结构的碎片化与规避式复杂化,而非建立起一个统一、可信、可替代美元的全球支付替代体系。
四、金融稳定与监管话语:示范宣示与制度短板并存
潘行长文章强调以强有力的IMF为核心、强化监管一致性,并以中国的资管新规、存款保险与SIFI监管作为示范。现实却更复杂:
- IMF的资源与治理改革是多方协商的政治过程。IMF高层与IMFC 在2025春季的讨论强调了份额调整与资源充足性,但相关实质性变更需成员国国内批准,并受主要经济体政治意志影响,不可能由单一倡议短期推动。
- 国内监管成就存在两面性:中国在资管新规、存款保险与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上确有进步,但同时长期存在的影子银行、地方隐性债务与房地产相关系统性风险没有简单“消除”,更多是以规则压缩与结构性调整的方式进行管理。把“落实国际规则”与“系统风险彻底化解”混为一谈,是过度乐观。国际评级机构、研究报告亦多次指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长期脆弱点,需要持续透明与外部验证,而非仅靠宣示。
结论:监管一致性与全球金融安全网需要广泛信任与长期制度建设;单靠“倡议”“示范”口径无法一锤定音。
五、治理改革:追求代表性与现实的摩擦
推动IMF/WB 等多边机构份额调整以反映新兴市场地位,是合理诉求,也是必要议程;但要看到两点现实:一是份额调整涉及既得利益国的国内程序,二是改革路径往往漫长且充满政治妥协。把“提高话语权”定位为单向可快速实现的目标,低估了国际制度变迁的摩擦。
不要被大话术遮住了制度与市场的脆弱现实
央行与国家层面的所谓“大倡议”,在塑造话语场、提高国际影响力方面确有其价值;但将宣示当成改革的全部,或把技术试点当成体系替代的核心证据,则是公共话语与政策判断中的两个常见误区。现实的货币与支付体系,是由市场信任、资产深度、法律保障与多边制度共同支撑的复合体;要改变它,需要的是耐心的制度建设、透明的规则、以及能够得到广泛国际采纳的可核验成果——而不是仅靠气势与口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