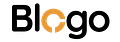小时候,有一位老者说过一句话:一个国家像一艘船,风来了靠顺风,风停了靠舵手。过去二十年里,中国靠着一连串“顺风”(人口红利、外需红利、外资与技术红利、房地产与投资红利)把经济这艘船推得很快。但当风向改变、红利退散时,我们发现:舵手不是稳住航向,而是在变换航道中反复试错,甚至把船头一再对着风浪。结果是:红利一个个消失,风险逐步积累。本文聚焦于两个关键词——“团派”与“李强”路径,试图回答:他们的20年,如何让中国“好事占尽、坏事做绝”。为什么红利纷纷消失。
一、谁是“团派”和李强?
“团派”(Communist Youth League faction,俗称“团派”)长期被用来指代中共内一批来自共青团系统、以温和务实与注重民生著称的干部群体;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干部培养、行政治理上形成一股力量。维基百科
李强:出身地方干部,长期在浙江、上海等地任职,被视为短期实用主义的经济管理者。2023年出任国务院总理,其政治经历和风格被外界视为“重视地方经验、讲求短期效果”。维基百科
二、红利为何一个个消失?
1)人口红利:结构性失衡,年轻劳动力在流失
曾经的“人口红利”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底层条件;如今少子化、老龄化趋势明显,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,城市青年就业压力剧增,失业率攀高成为硬指标(官方统计与媒体多次报道青年失业率在高位波动)。青年就业长期结构性弱化,意味着消费前景与人力成本优势双双受损。Reuters
2)外需/美国红利被切割:技术封锁与出口阻力
中国长期依赖外需尤其是美欧市场的高强度需求与技术输入。但近年来,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(尤其在半导体与高端芯片领域)切断了重要技术上游与出口便利,严重影响中国向“高端制造”跃升的路径。政策对抗化解了红利;不是外部压力的“始作俑者”,而是长期依赖外部体系且在关键时刻选择对抗,导致阵地被迅速收窄。Reuters+1
3)日本与其他东亚合作的裂痕:供应链和投资撤离
日本企业和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地缘政治和经营风险考虑,开始将产能向东南亚转移并“脱钩”中国。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:它有疫情冲击、政治风险评估与长期战略再配置三重因素在背后。与日本等成熟资本的摩擦,使得中国在产业分工中的“稳定合作伙伴”地位被侵蚀,外部红利进一步减弱。Reuters+1
4)房地产与投资红利的透支与崩落
过去靠“卖地—建房—贷款—预售”模式形成的房地产增长,曾是地方财政和家庭财富感的重要来源。但“三道红线”监管、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(以恒大为代表的债务链条暴露)与居民购房信心下降,令房地产从“拉动器”瞬间成为系统性风险源。监管虽然有必要,但在节奏与补偿机制不足时,导致连锁倒逼、投资萎缩。Italy+1
5)金融与影子银行风险:泡沫化的救急工具
面对增长放缓,过去一年多的货币和财政宽松在一定程度上走向“靠资产价格托底”的道路,资本更多流向投机而非实产。地方债、隐性债务和影子金融体系累积,使得任何一个大的房地产或企业违约,都可能形成系统性震荡。若以泡沫维系繁荣,终局就是脆弱且昂贵的复苏。(参见对地方债与金融监管的多份分析性研究。)Council on Economic Policies
6)政策与社会心态:从“向上”到“躺平/焦虑”
当社会预期从“未来更好”转向“就业难、房难、钱难”,年轻人信心被侵蚀,消费转弱,创新意愿下降。心态的变化不是小事——它影响的是创业、消费和税收收入的三条长期基础线。
三、团派与李强路径:好事占尽,坏事做绝——怎一个“绝”字了得
这里的论点不是人身攻击,而是把“好事占尽、坏事做绝”作为一种政策逻辑的概括:
-
好事占尽:在过去的土地财政、出口扩张、投资驱动的阶段,地方官员与以团派为代表的官僚群体善于抓住短期增长机会,用“速度”和“规模”把红利快速收割,使升迁与政绩显著。结果是短期GDP漂亮、就业数据好看、地方财政暂时宽裕。
-
坏事做绝:但长期看,这种“先吃快活再还债”的政绩文化,会忽视负外部性:环境破坏、隐性债务、过度杠杆、产业空心化、以及对制度性改革的拖延。等到外部环境恶化(疫情、贸易摩擦、技术封锁)时,累积的问题就会“集中爆发”。
把这套逻辑套到李强和“团派”路径上,我们可以看到:强调“稳增长、地方主导、短期见效”的政策组合在顺风时确实收获巨大——这就是“好事占尽”;但当顺风不再,他们没有足够的制度储备和战略耐心去做长期纠偏,结果就是“坏事做绝”。(这是一种对政策路径与激励机制的批评,而不是对个人的品德指控。)维基百科+1
四、央行买黄金:信任与脱美元化的焦虑信号
近年来,中国央行对黄金储备的持续增持引发外界关注——其逻辑是明显的:分散外汇储备风险、对冲美元霸权与美债不确定性。央行大举买金,是对全球金融体系不确定性的理性对冲,但它也说明: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系统性焦虑——当你认为“外部体系不能长期信赖”,你便倾向于规避而非合作。可问题在于:黄金是价值储藏,却不能直接替代美元在全球结算体系中的流通与信用功能。换言之,买黄金是防御性动作,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、市场和制度被动的问题。彭博社
五、金融泡沫、表面繁荣与真实增长之间的鸿沟
-
泡沫化的救市:当真实增长乏力,政策往往倾向用宽松和资产托底来维持表面繁荣。这可能短期稳住GDP,但会把问题留给未来:资产价格泡沫、债务层层传递、风险偏好扭曲。
-
结构性改革缺失:真正能补回“红利消失”的,是制度改革、产权保护、市场开放与技术创新生态。若把资源继续放在“保岗保房、以货币政策和信贷掩盖结构问题”上,只会把风险从经济下行转化为金融系统化风险。
(关于金融监管和三道红线等政策的分析,见多家金融机构与研究机构的总结。)Council on Economic Policies+1
六、对日、对美的强硬姿态,加速红利流失
对外的强硬可以短期凝聚国内认同,但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今天,强硬常常伴随代价:
-
市场代价:与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在技术、资本与市场上发生对抗,会让中国失去重要的增长渠道(高端设备、核心零部件、外部市场需求)。Reuters+1
-
供应链代价:外国企业为了分散风险,会迁出或减少在华投资,供应链改道至东南亚等地,从而侵蚀制造与就业基础。东盟交易所
-
制度与信任代价:政治风险上升会让长期资本更谨慎,技术合作变少,人才流动也受限——这是对创新最直接的伤害。
一句话:把对抗当成常态,等于把以前建立在互依互惠上的“红利市场”一寸寸关上门。
七、结论与警示
对决策层的告诫
-
不要把短期政绩当成长期国运。用房地产和高强度投资堆出来的数字,替代不了创新驱动和制度竞争力。
-
不要把外部压力当成常态化理由转向孤立。与其把外部合作角逐为“威胁”,不如把合作变成“互惠的战略资产”。
-
补制度短板:产权保护、司法独立、金融透明、市场准入——这些是未来二十年能否创造真正红利的基础。
对公众的提醒
-
警惕“表面繁荣”:当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产价格和政府干预,普通人应识别风险,不把所有财富押在房产与A股或其他单一金融工具上。
-
保持理性监督:公众舆论与市场监督,是促使政策回归理性的重要力量。让讨论更开放,能促进更好的政策纠偏。
尾声:红利消失后,谁来把舵
“好事占尽、坏事做绝”的批评重在指出激励与制度的失衡:当一方在顺风时收割过多、在逆风时又缺乏韧性,国家长远利益便会被侵蚀。团派与李强路径的“短期实用主义”在一定历史阶段确有其合理性,但当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时,简单复制过去的逻辑只会让红利更快流失。
历史的舵手不是一味固守旧法,而在风向变化时敢于学习、调整与开放。否则,再多的短期政绩也难换来国家的长期稳健与人民的真实福祉。